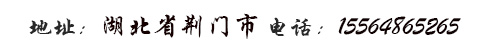失落东北磨豆腐的哑巴舅舅澎湃在线
|
编者按:本书为“网易人间”关于美食记忆的精华文化合集,以不同的角度和风格,走进70后80后的记忆深处,以最为难忘的味觉记忆,呈现几十年来美食的多元化和丰富性。 文:小杜/独立文学创作者 --1 母亲来美国几个月,我带她去了无数次华人超市,最常买的就是豆腐:水豆腐、嫩豆腐、老豆腐、冻豆腐、油豆腐、糯米豆腐、麻油豆腐……再加上豆腐干豆腐乳之类,我的冰箱整整一层都是各种豆腐。 我劝母亲:“豆腐含太多大豆异黄酮,对身体不好,尤其是过了更年期。” 她不听,还是不停地往回买。可回来吃两口就又不吃了,放冰箱里,等想起来了再下锅。有些过了保质期,严重的长起了一撮撮的白毛,不严重的虽表面看不出什么,但还是被我扔了。 看母亲买豆腐的固执劲儿,总让我觉得她不是老了,就是想回国了。 “妈,豆腐有那么好吃?” “说不上好吃不好吃,就是吃起来不对劲。” “美国这边的豆腐不对劲?” “国内豆腐现在也不对劲。再说美国的豆腐不也是从国内进口的么。” 看来是她老了。我不再说什么,任由她去买吧。 2 后来有一次,听母亲说起她的一个小表舅,我才明白,她为什么那么爱吃豆腐。 母亲和小表舅小时候,一个住县城,一个住农场,隔着三四十里地。 姥爷去世得早,六个孩子全靠姥姥一手拉扯大——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手拉扯大,日军侵略时姥姥被炸掉了一只胳膊。姥姥家虽在县城,但条件极差。小表舅家在农场磨豆腐,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买卖。故两家间走动,以母亲去小表舅家居多。 母亲那时人小,又是女孩家,小表舅家留吃饭,姥姥从来不让她上桌。不上桌就没有新闷的大米饭,连新蒸的豆腐都没有,只有一块烤地瓜和一碗撒了盐的豆腐渣——固然热乎,但毕竟也还是豆腐渣。 当时,小表舅比母亲矮半头,还是个哑巴。 两岁时,家里大人背着小表舅去林子里挖蘑菇,遇见了黄大仙,大人孩子回家都发了一场烧。大人躺了两天,起来继续下地干活,孩子却成了哑巴。哑巴表舅见母亲捧着一碗豆腐渣,就自己去切了半块蒸豆腐,撒上葱花儿酱花儿,偷偷端给他的表外甥女。 那蒸豆腐味道如何?用母亲的话就是,“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”。 偶尔小表舅也来姥姥家串门儿,母亲就给他留一碗大米饭煳锅巴,蘸了酱油大口大口吃。不过还是母亲去他家多,所以偷偷端出来的蒸豆腐远多过煳锅巴。具体多了多少次,母亲说她到现在都还记得,可见有些事越老越放不下。 时过境迁,半个世纪过去。 华人超市里摆的豆腐划分得极细,单就老嫩的程度,就分firm、mediumfirm、soft、mediumsoft、silk、mediumsilk六种。母亲把它们逐一买回来,挨个蒸上一遍,撒上葱花和豆鼓酱,全是为了寻找当年“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”的感觉。 可能找回来么?看看我冰箱那些长了毛的盒子就知道了。 3 中学毕业后,母亲被分配到县第一副食品公司,简称“副食”。当时母亲还不到二十岁,在副食当售货员,穿着公家发的白大褂和白口罩,整天在几颗猪脑袋和一大堆心肝肺之间翩翩起舞。 工作倒不怎么忙,但渐渐她就不大和姥姥去农场了。究其原因,除了她正和父亲热恋,再就是副食的猪头肉实在好过小表舅家的蒸豆腐太多了。 小表舅也不再磨豆腐,他跑到县里搞起了个体户。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创业的头脑,而实在是时代不由人:生活改善了,条件发展了,磨豆腐不再是什么神乎其技的手艺,农场和县里冒出好几家卖豆腐的,生意便不似从前那么好做了。 再说他又是个哑巴,一块块的雪白豆腐,都让家里会吆喝的人推出去卖了,挣多挣少他一点数也没有,于是就没完没了地跟表舅姥爷比画,要自立门户。 可是他一个农场长大的哑巴小子,能干啥呢?于是,他以去姥姥家串门为由,跑了好多趟县城。除了往农场带回“副食”的香肠和猪耳朵,他还窥探到县城的一个秘密,那便是刚建起来的菜市场。 菜市场是一个神奇的存在,倒扣着的塑料大棚,摩肩接踵的人,和着吆喝、叫卖、喊秤、剁排骨声,各种讨价还价,杀鸡剁脑袋,两个女人对骂,地当中是两条大鲫瓜子,啪啪啪地甩着尾巴。 而且这里每天都那么热闹,连礼拜天都是,农场越闲,县里的菜市场就越热闹。 这里只有一样让他感到沮丧,便是有整整两排玻璃柜子在卖豆腐脑豆浆干豆腐,一切跟豆腐有关的东西这里都有。可他从小到大只有磨豆腐一样本事,在这繁花似锦的菜市场却派不上用场。他垂头丧气回到农场。 他蹲在晚春的黑泥上,用刀子画啊画啊,把自己支离破碎的县城梦讲给表外甥女。母亲却笑了。不是因为自己新烫了头发,也不是和父亲订了婚,而是今天她要来给小表舅说亲:“人家也在‘副食’上班儿,年龄偏大没几岁,脸上稍微有点麻子,也是后天才哑的,但这些算啥?人家愿意帮咱办县里户口。” 县里户口,偏大没几岁,麻子,副食,公家……这些事物在农场的人嘴里传来传去,把表舅和一个同样说不出话的女人串在一起。 他结婚了。一个哑巴,在县里自立了门户,整个农场谁能想到呢。 4 表舅如愿以偿,很快在县菜市场摆起了摊子。 最初是卖生豆芽儿,在地窖里摆好一个个塑料编织口袋,一口袋底儿的豆子,润上一点水,用砂子压,用石头压,用面盆压,压上两三天,豆芽就滋滋滋发出来了。一口袋一口袋的,白白胖胖的,煞是好看。趁天没亮,就赶紧骑三轮车把先发好的送到菜市场。立了牌子标价,不讲价,不谎秤,人称“哑巴豆芽”,没多久就在县里传开了。赶上逢年过节,一天能卖两三编织袋。 这事业只一样不好:起早贪黑,风里来雨里去,忒遭罪。好在年轻,体格儿好,哑巴舅妈又疼他,天天中午跑去菜市场送饭,铝制饭盒里是蛋炒饭,撒了牛肉丁儿,小暖壶里是浆子,加了糖掺了牛奶。不像旁边卖蒜苗的两口子,顿顿饭茶蛋就地瓜干往下噎。 十生百,百生千,如此两三年下来,两口子成了万元户。眼见着表舅妈的肚子一天天圆了起来,没多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,呱呱落地,哭得又响又亮。 也是同一年,我出生了。小时候,我经常去我这个同龄不同辈的小舅家玩,除了屋里屋外一股豆芽味儿,其他都挺好。饼干小人儿酥管够吃,红白机随便打,从早上打到晚上,打到两眼发直,打到母亲过来拧我耳朵才能拉回家。 记得有一年春节,两个不说话的大人领着一个说个不停的小人儿,来我姥姥家拜年。电视里重播春晚,有个小品说“造导弹的不如煮茶蛋的”,大人听了一笑了之,我那个同龄的小舅却豁着牙续道:“煮茶蛋的不如生豆芽儿的!” 童音响脆,掷地有声,众亲戚纷纷向哑巴两口子道喜。表舅妈捂着嘴笑,表舅一把抱起儿子亲个没完。 当时“副食”还没黄,但已入不敷出。猪头肉猪耳朵卖不动,又怕坏,就顶奖金发给职工,连发了半年,发得我一看到猪耳朵就犯恶心。父亲也要调工作,所以他和母亲压力都很大。 我却满脑子都是红白机,心想我家要是也屋里屋外一股豆芽味儿就好了。 5 至于母亲的哑巴表舅,房子越盖越大,生意也越做越大,从豆芽儿扩展到各种蔬菜水果,与此对比的是县里的“副食”,彻底黄了,连房子都快扒了,只剩下几颗目瞪口呆的猪头和一堆干巴巴的猪耳朵。 哑巴舅妈干脆和表舅在菜市场斜对面盘下一处门市房,门口还摆了一大音箱,“老兴隆蔬菜水果小世界即日起正式开业,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光临,新进日本原产红富士苹果,八五折优惠,欲购从速……” 至于那位和我同龄的小舅,也许是小时候说话太多了,一进入青春期反倒变得少言寡语了。要么不张口,要么一张口就骂人。他的哑巴妈妈新烫了头发,穿梭于“老兴隆”和各种牌局之间,没心思下厨做饭,小舅就叼着双汇火腿肠,像是衔着一根粉色的雪茄,整天在菜市场里游荡。那时候,火腿肠两块五一根,县里条件一般的孩子轻易不买。我问过小舅,火腿肠到底是肥肉还是瘦肉。他正一口一口往下咬塑料肠衣,咬完再一口一口往外吐,弄的满嘴都是绛红色:“他妈的全是粉面子!” 那时,我很羡慕小舅可以说随便脏话,甚至在哑巴父母面前也能吐出那些字眼儿。不知道是整个菜市场到处都充斥着那些字眼儿,还是他父母觉得一个人能张口说话就算莫大福分了。 满嘴脏话的小舅很快和菜市场的成年混混熟络起来。在县一中侧门口,他变戏法儿似的从土绿色军挎里抽出一把甩刀,单挑了几个吆五喝六的小流氓,成为全校的偶像,哪里还有我近身的份儿。 那时一中的保安姓谭,挺年轻,但天生谢顶,脑袋又有点歪。全一中的师生校长教导主任加起来,小舅也没把谁放在眼里,除了这个谭老歪。只是因为每次小舅闯祸进了警局,都是这谭老歪把他拎出来的。 所以在一中昏暗的厕所里,小舅总是递上一支刚点着的石林烟:“老谭,抽吧。” 尽管一出学校就跑去菜市场厮混,但小舅的成绩也没那么坏,至少家里花钱读个高中不成问题。但县里高中敢不敢收他,却是另外一个问题。 初三那年夏天,他终于替高中解决了这个头疼的问题:在电子乐轰鸣的迪厅,他把甩刀插进了一个醉鬼的太阳穴,理由是那家伙居然把他当成了一个女的。 这也难怪,彼时小舅虽发育起来,但面色苍白,双腿比双眼还要细长,即使艳阳高照,他浑身上下也透着一股阴冷的狠劲儿。那醉鬼是个成年混混,在道上贩卖来自南方的摇头丸。而我的小舅,才刚刚进入变声期。 事后,有人说那是一柄三叶甩刀,有人说是弹簧刀,还有人声称那是正儿八经的警匕。不管是什么刀,故事的最后,小舅一脚踹开窗子,从三层高的迪厅跳出去了。 尽管家里能砸得起钱,也愿意砸钱,但还是摆不平这祸事。“老兴隆”生意暂停,哑巴夫妻好像两只绝望的蜘蛛,吐尽了所有的关系网,也只是徒劳。走投无路之际,他们把儿子送到了农场,哑巴表舅的老家。 没多久,谭老歪推开了他家的大门。 根据谭老歪的说法,事儿闹得确实有点大发了,但也不是不能摆平,因为“摇头丸断了,咱家孩子其实给县里除了一害”。 在哑巴表舅家,谭老歪问:“咱家到底能掏多少钱?” 表舅排出四打一百元的票子。 谭老歪没吭声,闷头抽烟。 表舅急了,咿咿呀呀比画一番,舅妈急了,又从里屋拿出四打百元票子。这回是用塑料纸包着的,上面粘着泥,一股潮气,明显是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。 “操,用不了这么多!”谭老歪把四打票子塞进牛皮纸大信封,转身就走。 6 买回一条命的小舅被一辆农用双排座送回县城,在迪厅舞厅过完了他的变声期。谭老歪将哑巴表舅家那笔“人情费”扣了一半,自己在县里打点,从此扶摇直上,没多久就穿上了制服。 “谭大副”,县里人都这么称呼。在警区或拘留所,每次不期而遇,小舅依旧叫他“老谭”,然后递上一支硬中华。 后来,老谭往他家拨了电话,说这样下去你家孩子早晚也会变成县里一害。 哑巴父母在电话里自然是沉默的。“要不让孩子当兵吧,我给找人。”老谭说。 老谭说话算话,这兵当的倒真没花太多钱,而且是海军,南沙群岛,理由是“南沙离咱家够远,孩子轻易没法儿往家跑”。 所以我读高中那年,小舅就去参军了。等我考上大学,他升士官。他退伍回县里,我已拿到签证出国了。 小舅家也起了很多变故。 先是有年冬天“老兴隆”被一把火烧没了。倒不是哑巴两口子不小心,而是菜市场被什么人趁半夜点着了,火借风势,咆哮奔腾在整个南二道街区的夜空,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罢休。整个南二道街被烧落了架,烧得县里整个冬天都有那么一股焦臭味。 好在大火没烧退哑巴表舅的雄心,他干脆把事业从倒腾蔬菜升级为倒腾木材。买了辆“东风”大卡,把农场的松树林子一株一株放倒,锯成板条,再拉到省城,卖给南方来的“大老板”们。 我母亲曾极力反对这事,说这是犯法的,一旦抓着了就进去了。哑巴表舅却摆手笑她。他有他的信心,便是谭老歪。因着他儿子的那场祸事,他和“谭大副”成了老铁。 母亲又指望舅妈劝劝,可人家正热心于整容和打麻将,一桌三个舅妈那种年龄的女人,都是手里有闲钱的,外加一个年轻小伙,个儿高,皮肤白净,爱说爱笑,一笑还有两酒窝。 据说,舅妈麻将原本打得很好,但自从有了这小伙凑局,舅妈的牌就有点乱了,小伙子一讲笑话她就笑,一笑就给人家点炮。输点钱无所谓,关键是开心。舅妈虽有点发福,但把脸上麻子点下去了,又割了双眼皮儿,拾掇拾掇也挺耐看。 后来,她还往家添了卡拉OK,打完牌就在饭店订了锅烙或水煮鱼,请大伙去玩儿。那小伙子专唱刘德华的《忘情水》。几个中年女人嘻嘻哈哈喝酒吃肉,只有哑巴舅妈对着在松下大彩电里嘴巴一张一合的刘德华出神。 表舅这边跑了几趟省城,木材事业竟也做起来了。他也学南方的“大老板”,新买了款爱立信手机别在腰间,也是刘德华做的广告,“事业我一定努力,对你我永不放弃。”可他是个哑巴,没法用爱立信谈生意,只能用来听歌。 还真有人在爱立信里给表舅唱歌。 省城到县城八百里国道上,有一个鸡鱼馆的女老板,据说丈夫被车撞死了,她才从老板娘变成了老板。女老板除了给表舅亲自炖鸡炖鱼,还揉肩搓背,给他唱歌。在枕边唱,在爱立信里头唱。开着东风大卡,听着情人唱歌,八百里的国道大概都跟着旖旎起来。 后来,女老板就问表舅,说要不你把倒腾红松的款子都取出来,我这边认识个熟人,着急抬钱,三分半的利。抬完这钱,咱俩就一起过吧。 表舅本来还有点犹豫,可一回家发现有个小伙对着自己老婆唱《忘情水》,他就把钱都取出来,让女老板都给抬进去了。 结果,女老板转眼就在爱立信里消失了,表舅急了,去鸡鱼馆里找人,却只有几个拎着西瓜刀的老爷儿们。 本来表舅还可以找老谭,可惜那年严打,“谭大副”横尸我们县夜总会,浑身都是砂枪轰出来的窟窿眼儿,谁也说不清是谁干的。 当时县里不少有钱人都在闹离婚。母亲说这下完了,表舅和舅妈够呛了,父亲却说肯定离不了。钱要还在,那肯定离了。现在钱没了,又是对儿哑巴,离了找谁过呀? 果真没离。 表舅在家里跪到第二天,儿子从南沙群岛打来电话,说眼看要退伍转业了,要他们赶紧再汇笔钱,好托人找关系。舅妈一把抱住丈夫,两口子抽泣起来,发出一种只有哑巴才能发出的呜咽。 卖掉东风大卡,一大半儿的钱汇去海南岛,一小半儿租了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门市房,“夫妻二人烧烤涮”又起来了。 7 很可惜,小舅退伍后只能回县里,因为家里的钱到底还是没跟上。 小舅被南海的风吹得又黑又瘦,穿着一身帅气的海军服,站在县里灰秃秃的南二道街上,挺拔而突兀。 南二道街的拐角是“成功驾校”。按照哑巴两口子的设想,一张驾驶证再加一笔退伍转业费,足以将儿子变成一个大卡司机,往来于省城与县城之间,从头再来,再造他们家倒腾木材的辉煌。可是小舅却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。就像每一个在外面闯过的年轻人,他对这县城有股莫名的厌恶。 而哑巴表舅的烧烤涮生意原本就惨淡,又被新开业的韩式烧烤城给顶了,每天也就中午有几个小学生过来嚷嚷着烤两毛蛋而已。这更让小舅下定决心,拿到驾照后一走了之。至于将去何方,他没具体想过:“反正越远越他妈好,越往南越他妈好。” 在满是轮胎印迹的大院里,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。 我是听母亲说的,依照母亲的理解,这女人年纪轻轻就离过婚,家里又没钱,还是个独生女,惯得不像样,随便哪一样都是能杀死一桩婚姻的毒药。至于那女人到底是怎么看上小舅的,母亲更是没法理解。 小舅一结婚就和老婆去南方了,一个开烧鸭店,一个搞美容。 “都不是容易挣钱的营生,”母亲摇头叹道,“在县里干不一样么?跟老爹老娘一起过还相互有个照应,不挺好么?” “妈,我要在县里一直待着,你觉得好么?” 母亲沉默。 母亲在美国过得挺高兴的。她在国内虽是无神论,但在美国却总让我带她去教会,因为那里有说有笑,有布道有唱诗,有钢琴有管风琴,不分国籍,不分肤色,无论贫富,彼此兄弟姊妹相称,感觉比我们县里好多了。 教会还经常搞聚餐,大节小庆的,每家带一道菜,凑一凑就是十好几桌儿,又没人喝酒抽烟打麻将,母亲很是喜欢。母亲烧的菜里,必有一道带豆腐的,麻辣豆腐,尖椒干豆腐,肉末煎豆腐,不一而足。 虽只是家常菜,在国内难登大雅,但教会里的美国人都吃得竖大拇指:“ChineseTofuissuper!(中国豆腐太牛啦!)” 即使是中国人,在美国待得久了,口也就不刁了,也都说母亲手艺好。可我知道她对自己烧的豆腐越来越不满意,离当年在她表舅家吃蒸豆腐那“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”的感觉越来越远。 去年感恩节,我陪母亲去商场买衣服,我坐在女试衣间对面的沙发椅上苦等,各种肤色各种高矮胖瘦的女人在眼前出来进去。 母亲从试衣间里出来了,双手空空。 “妈,挑那么一大堆还没合适的?” “国内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dougua.com/ddqyx/1966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学中医有什么好处可以护你周全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