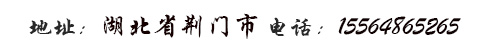东坡书院游记
|
历史上的海南岛地处边陲、孤悬海外、闭塞落后、距离京城几千里,“鸟飞犹用半年程”,因此中原人称之为“蛮荒瘴炎之地”,死囚流放之所。唐宋以来,大批名臣巨儒被贬海岛,形成了一种“贬官文化”,省会海口的“五公祠”就是见证。在所有被贬海南的人士中,对海南的历史进程、风俗习惯影响最大、最有成就的无疑当推苏东坡,苏东坡在海南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原一般,今天在海南有一处纪念东坡的知名胜地,就是位于儋州的东坡书院。 苏东坡一生为政建树颇多,但屡遭打击和陷害,宦途多舛,先后三次遭贬。第一次是发落在湖北黄州,第二次是贬到了岭南的惠州,最后一次是海南岛的儋州。被贬惠州时,他写了一首诗:“白头萧散满霜风,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此诗传到京城开封后,被当时的宰相、之前的好友如今的“政敌”章惇看见了,此人非常不高兴,心想苏轼居然还这样安逸,还能“春睡美”,便盘算着将苏轼贬到更坏的地方,于是下令将其贬到了海南儋州。于是,公元年,61岁的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,被一叶孤舟送过了琼州海峡,登上了海南岛。流放海南,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,当时,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,面对一个原始落后、暗无天日、蛇蝎横行、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,是何等的凄惨与悲凉?但是,苏东坡坚强乐观,克服种种困难,硬是把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“诗和远方”。 出于对中国历史上这位传奇人物的崇敬,也出于对大文豪九百年前如何将海南蛮荒之地变成“诗和远方”的好奇,庚子季夏时分,我邀请我的一位兄弟,亦是本校历史组的同仁,一起追随着苏东坡的足迹,来到了海南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。 (东坡书院游客接待中心) 或许是受东坡词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的鼓舞,我们不畏炎热天气和两百余公里的长途,一路驾车到达书院游客接待中心,购票进入了景区,包括主体建筑及外围景观,东坡书院的建设规模达平方米之巨。我们沿着蜿蜒曲折、古色古香的雕栏石桥,经过的宽阔碧绿的莲池,再穿过一片精致仿古的竹林茅房,才到达书院的正门。正门上方悬挂黑色字匾“东坡书院”,这几个字为清代书法家张绩的手迹,字体端正、刚劲有力,实有东坡“遗风”,东坡书院,延续近千年的文化圣地,海南重要的历史坐标,我们来了。 (东坡书院正门) 进大门后,首先看到的是载酒亭(亭子名称由来,见后文解析),载酒亭为重桅歇山顶结构,上下两层,上层四角,下层八角,各角相错,四角翘起呈欲飞之势,亭中顶部雕刻描绘了苏东坡居住儋州三年的生活情景图录。 (载酒亭) 穿过载酒亭,浓浓的书卷气息便扑面而来,因为眼前便是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,也是东坡书院的前身——载酒堂。堂中小院古木幽茂,群芳竞秀,院门正中有一块"先生悦之"的大匾,两旁对联写的是:生面重开更有客吟诗对此茂林修竹;芳踪如晤看执经问难依然沂水春风。从对联,我们不难想象当年东坡在此地讲学,文人相聚的书香盛况。史料记载,年,苏轼到达此地后,昌化(儋州)军使张中知道苏轼是一代文豪,因此不敢怠慢,安排苏轼及幼子苏过“住官房,吃官粮”。后来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,听说苏轼住在昌化官舍,遂谴使渡海,逐出官舍(苏轼当时是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远谪儋州的),张中也因此受到处分,从此苏轼便开始过着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、夏无寒泉”的悲惨生活。载酒堂原址为当地人士黎子云的宅地,苏轼一日与张中同访黎子云,与当地人士相聚一起,众人提议,为方便苏轼讲学,请在黎子云处建一讲堂。苏轼欣然赞许,也很喜欢这个住处,根据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,为房屋取名“载酒堂”(前文提到的载酒亭的名字,也由此而来),从此,这里便成了当年苏轼会见亲朋好友、为黎汉各族讲学授业的地方,黎子云也成为了苏轼在海南最好的朋友。岁月变迁,明朝嘉靖二十七年(年),“载酒堂”更名为“东坡书院″,几经沧桑,多番修缮,流传发展至今。 (载酒堂大殿) 载酒堂大殿正中有一组东坡讲学的塑像,塑像的中间坐的是东坡本人,右边一位是好友黎子云,站在东坡先生后边的是他的小儿子苏过,这组塑像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东坡先生当年那种谆谆善诱、诲人不倦的形象。史料记载,苏东坡在载酒堂设教徒,自编讲义,把《书传》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等著作作为教材讲授,以诗书礼乐之数转化其风俗,由于苏东坡经常在载酒堂“传道授业解惑”,儋州和周边地区也兴起了求学崇文之风。对这种求学之风,苏东坡颇为欣赏和满足,曾作诗一首,记载了一次听到附近儿童读书的场景及心声——“引书与相知,置酒仍独斟。可以侑我醉,琅然如王琴。”东坡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,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,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,就是东坡先生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,东坡获赦北归后,他的弟子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,受其影响,海南士子连续不断地考上了功名,有宋一代,海南共出了12位进士,使“蛮荒之地”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。史书指出,东坡后“十余年文学彬彬,科目自隋莫胜于进士,琼在四榜连破天荒”,”自昔,邵学之制,则始于庆历,详于谆熙有自来矣。人物之盛,有宋时有杨誉苏门者焉,有声驰甲科者焉,亦有文坛乡帮者焉。”东坡作为海南文化的启蒙者对海南文化的发展,作出了重大贡献,在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 (东坡讲学) 在载酒堂后侧大殿里,存有多幅东坡本人及历代名家的字画、对联,或为后人依字体雕刻而成的木匾,或为高仿制品,其中,东坡的经典代表作——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高仿版《黄州寒食帖》(真迹现存台北故宫院,东坡书院的陈列按真迹高仿),在大殿一侧的展柜里格外醒目。除此之外,大殿旁的厢房里,还保存着一些历代关于东坡的图书资料,皆弥足珍贵。 高仿版《黄州寒食帖》 参观完主体建筑载酒堂后,按照书院工作人员的建议,我们开始参观载酒堂两侧的园林。首先进入东园,踏进园门,便见一口古井,名为“钦帅泉”,得名于苏东坡曾任兵部尚书(即钦帅)。该古井历经千年而不干涸,为了方便八方游客体验古老的打水方式,古井旁放置了绑好粗绳的小木桶。我除了拍照留念,还体验了一番古法打水,将井水慢慢提上来,掬一捧自然鲜活之液擦拭脸庞,当泉水接触肌肤,其清澈沁凉让人神清气爽,感受非同一般,一旁的兄弟帮我录下了珍贵的视频……当年东坡居儋州,当地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,以致常年患病,为解除民众疾苦,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井,取水饮用,疾病便少了,此后,远近乡亲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,一时挖井成风,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塘水习惯。“钦帅泉”,就是东坡先生改变乡民饮水的见证!不但是饮水习惯,东坡先生居儋州时,对当地人的迷信、民族关系、生产劳动习俗等都曾做过积极的引导,通过他身体力行的倡导,改变了当地人的许多陋习。例如:当地人民缺少医药的知识,通常是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,为改变当地人的这种陋习,苏轼对药物进行了研究,并为百姓开方治病。他还曾专门向居住在广州城的王敏仲索来黑豆,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鼓,为民治病,自此以后,当地百姓纷纷种黑豆,后人称为“东坡黑豆”…… (钦帅泉) 过古井,我们又在东园参观了钦帅堂、春牛雕像、狗仔花、怀贤亭,东坡私塾、望京阁、劝耕圃……东园景点较多,给我印象最深的,除古井外,则是园内的几株“狗仔花”。园中通往私塾的小道旁,种了几盆花,刚开始我并没在意,但通过阅读侧立在旁的介绍栏,狗仔花这个名字便吸引了我,栏中关于苏东坡与狗仔花的历史故事,更是令我驻足细品。故事介绍——“有一天苏东坡去王安石相府拜访,恰逢王安石上朝未归,东坡便到书房等待,见案桌上铺笺写着明月当空叫,五犬卧花心”这样一句诗,苏东坡瞧了又瞧,好生质疑,心想明月只有照,哪能叫“狗只能卧在花荫,哪能卧在花心”他认为王安石的这句诗不合事理,于是提笔一改,将诗句改为“明月当空照,五犬卧花荫”,然后离开相府。王安石下朝回府看到诗稿被改,认出是苏东坡的笔迹,只是微微一笑,未置可否。后来,苏东坡谪居儋州,一天夜晩,明月当空,苏东坡走出桄榔庵漫步赏月,忽听到有鸟儿啼叫,清脆悦耳,回荡夜空,遂问一同赏月的黎子云,黎子云告诉他这是“明月鸟”,每当月朗星稀,“明月鸟”就会腾飞天空,欢叫不息。不久东坡又在当地见到一种花蕊极似五只小狗的“狗仔花”,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王安石所写的“明月”是一种鸟,而“五犬”是狗仔花的花蕊,知道当年错改了王安石的诗,狗仔花也因这段轶事而名扬天下。”这个故事,既反映了苏东坡年轻时的耿直个性,亦体现了他注重观察自然、不断反思的学习品质,给后人带来了许多启示。狗仔花本微不足道,因为有了与儋州有关的名人轶事,承载了更多的人文意趣,美丽更加添色。 (狗仔花) (东园局部) 从东园参观完毕,转至西园,有一座苏东坡的笠屐铜像格外醒目,我和兄弟一踏进西园便在铜像前驻足。那栩栩如生的东坡铜像,矗立在姹紫嫣红的鲜花丛中,我看着头戴竹笠,脚蹬木屐的苏老先生,突然发觉苏东坡先生无论是神情还是长相,都酷似儋州本地人,难怪当年苏东坡自己也说”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“。头戴竹笠,脚蹬木屐,反映了东坡当年在儋州身体力行,辛勤劳作的场面,更反映了东坡积极改进海南生产劳动习惯的精神,苏轼在其著名《劝和农六首》诗中,苦口婆心,竭诚功说黎族同胞改变“不麦不稷”的状况,“改变朝射夜逐”这种单纯狩猎的劳动习惯,革除恶习,重视农耕,改进工具戮垦荒种植发展水稻生产……这些都是“春风化雨”般的恩德,其意义相对而言,要比他在徐州、杭州期间,帮助当地人民兴修水利更加重要。尽管面对被贬海岛的厄运,苏轼却能随遇而安、超然物外,并与海南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,当地百姓为了感谢先生恩德,经常为他送食物和粗布,供其饱肚御寒。每年腊月二十三是海南百姓的祭灶日,送灶神,他们在拜过神灵之后就把祭肉送给苏轼,正是因为有海南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,苏轼在海南才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。公元年,宋哲宗驾崩,宋徽宗即位,大赦天下。苏轼终于可以离开海南了,他很兴奋,可是,这三年的日子,他和海南,他和这里的乡民,早已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。离别时,他热泪盈眶,依依不舍,数不清的乡民,还有他的学生,站满了海边。苏轼流泪登船,永远地告别了海南,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六月二十日渡海》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?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不仅如此,苏轼在离开海南一年后回到镇江游金山寺时写下了一首《自题金山画像》,书写自己一生的贬谪生涯,题曰——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这充分地说明了他对三年海南生活的无限眷恋之情。我恭敬地瞻仰铜像,脑海中浮想起史书所载的段段东坡海南往事,情到深处,一首打油诗脱口而出,“千古悠悠载酒堂,书香翰墨绕桄榔。宦海无情累才士,儋耳奇绝永徜徉。” (笠屐铜像) (西园局部——槟榔树) 参观笠屐铜像毕,进入西园的陈列馆,再走过西庑廊、浏览沉香馆,书院各景基本参观完毕,我们才从西园跨出,返回大门载酒亭处稍歇,此时,思绪似乎才从千年前的宋朝跨越回来,刚才进行的,与其说是参观,不如说是穿越到过去的一场与大文豪的对话,一场收获颇丰的心灵对话。 (载酒亭、载酒堂侧景) 不知不觉,在东坡书院停留了三个小时,按照行程计划,我们将去中和古镇,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儋州,告别书院,仍意犹未尽,与兄弟一路上还在谈论着东坡,感怀着东坡精神。沿着笔直的旅游大道驶出,遥想东坡当年走过的那一条条异常艰难的路,内心豁然明白,苏东坡说的“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”及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绝非矫揉造作,而是在真情表白。因为他在海南岛的三年岁月,几乎是身处绝境,但在人生的最低谷阶段,他没有消沉,他看淡了仕途的起起落落,以至能在蛮荒之地随遇而安。他实践了自写词中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不为名权利所困,只讲究心灵的品味。这一生,与其羁绊于名缰利锁,不如在心里修篱种菊,儋州,成了东坡先生晚年安心的“家”。先生居庙堂之高不得意,处天涯之远亦不失意,他真正把生活过成了“诗和远方”。 书院之旅,收获颇丰,心之约会,相续无涯,东坡先生的“诗和远方”,激励着我,也必将激励着你,激励着每一个懂他的人! (李俊于年8月16日)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dougua.com/ddqyx/1423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哪些方具有清热解毒功效方剂每日五题练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