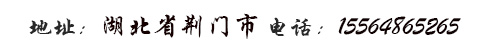发热案三则兼议退热十四法
|
发热案三则 ————兼议退热十四法 王某,女,21周岁,年2月12日来诊。主因低热伴肢体痉挛4月余来诊。 患者脑瘫病史,小脑受损,运动障碍,发育迟缓,身体羸瘦,不足30kg。 因外出受凉后,发热4个月不退,延中西医诊治俱不效,前医曾与服桂枝汤、竹叶石膏汤等。 现每日上午热势较重,37.8度左右,近5-6日调护不周而突发咳嗽,晨起明显,不恶寒,自汗盗汗,反酸腹胀,纳谷不佳,饮水亦觉胃部不适,口干口渴,二便尚调,肌张力高,颈项僵直不能自主控制,角弓反张,但神志尚清。舌色淡红,中部有些许浮苔,脉濡,沉按细弱略数。 析:本案患者素体气阴两虚,正气不足,感邪后前医误表,后又甘寒敛邪,故病迁延不愈。 今患者四肢僵急,角弓反张,自汗盗汗,口干口渴显是阴虚风动之象,调护不周复感外邪,咳嗽脉濡,是卫分之邪仍在。反酸腹胀,纳谷不佳,为胃气不足,宿食积滞。法以疏卫透邪、宣肺止咳、育阴补气,酌以消导。 疏方: 薄荷1g(后下)前胡6g杏仁9g浙贝母15g 苏梗6g青蒿3g鳖甲10g(先煎)白薇10g 地骨皮15g知母12g西洋参20g(单煎) 保和丸15g(包)生甘草3gX5付 服药一剂即热退,身静,反酸腹胀亦止,后用养阴补气和胃药善后。 方中前四味药直取赵绍琴方意,疏卫透邪,兼能宣降气机以止咳,加苏梗取其和胃调气兼能防诸药寒凉伤胃,其虽阴虚之体,然舌色淡红而未绛,恐久病阳气已伤,故稍加苏梗以护中州阳气,其余诸药无外乎扶正养阴和胃透邪之用。 虽吴鞠通有“阴虚欲痉者不可用青蒿鳖甲汤”之说,然其意在纯虚无邪,若此案之邪气仍在,专事养阴扶正岂无闭门留寇之嫌?而若汗表达邪势必伤阴耗气,其结果必定是越汗表气越虚,越易复感外邪。故养阴兼以透表,“在卫汗之可也”。 01朱某,鲐背之年。年3月28日入院。主诉:间断发热2周,咳嗽咳痰1周。 患者2周前住院时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,体温波动在36.4-37.3℃之间,多发生于午后及夜间,经抗感染及柴胡汤、青蒿鳖甲汤等治疗后未见明显好转。1周前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,痰黄量多。体温波动在37.0-38.5℃之间。 年3月28日查血常规示:白细胞3.4×/L,中性粒百分比56%,CRP:14.01mg/L。 胸片提示:两肺感染可能,左侧少许胸腔积液。 刻下:午后及夜间低热,咳嗽咳痰,痰黄量多,咽中不适。口干欲饮水,口中稍黏,小便自利,大便偏干。舌胖大而暗苔薄而少有剥脱,脉弦滑浮取弦细略数,左寸沉弱。查体:腹软无压痛。 诊断:1.社区获得性肺炎 2.支气管扩张 3.白细胞减少症 4.高血压3级很高危 5.陈旧性脑梗塞 析:本案患者午后及夜间身热不退,与阴分伏热、阳明热结、瘀血发热有相似之处。 但仔细辨之,其舌胖大,小便自利,非典型热伏阴分之舌瘦而红、小便短小、脉细数; 其低热而腹部柔软,非阳明热结之潮热、濈然汗出、脉沉实; 其口渴欲饮,非瘀血之但与漱水不欲咽或渴而不多饮。 故综合分析,当为陈士铎所言之心气不足,《辨证录》云:“心虚则火起心包而口渴。夫心与小肠为表里,水入心而心即移水于小肠,故小便自利也。” 心虚则生虚热,故欲饮水而灭热邪,但心气已虚,无力引水而救火,故水从其润下之性则直走小肠而见小便自利。 舌胖大,苔薄而剥,为气阴两虚之象;脉象左寸沉弱,更是心气不足之象。又因患者久病体弱而邪气乘虚入阴分,则午后及夜晚发热;按脉弦滑是素体仍有痰湿,复被外邪所扰故咳嗽咳痰仍在;舌暗则是久病入络又兼有血脉瘀滞之象。故以心气阴不足为主,以邪伏阴分及瘀血为辅。 法以补气养阴透邪、化痰祛湿活血,方以陈士铎清热散加减: 麦冬60g茯苓30g银柴胡24g桂枝9g 牡丹皮12g桃仁15g太子参30g鳖甲20g 地骨皮30g青蒿9g知母18g浙贝母30g 神曲20gX3付 二诊:年4月1日。服上方后,当日夜间即无发热,口干及咳嗽咳痰较前好转。现略觉喉中有痰,痰黏色白而难咳。头目不清,大便稍不成形。复查血常规示:白细胞4.4×/L,中性粒百分比58%,CRP:2.46mg/L。 处方如下:麦冬30g,茯苓15g,银柴胡24g,桂枝6g,丹皮12g,红花10g,太子参30g,浙贝母30g,海浮石30g,佩兰10g,山药30g,胆南星6g。4付。后患者症状较前明显好转,于年4月4日出院。 按:清热散为陈氏治心虚发热之方,其主治症状为“冬月伤寒,身热五六日不解,谵语声低,口渴欲饮,小便自利,安然欲卧”。发热、口渴欲饮及小便自利为其主证。 清热散,重用麦冬以补心气,兼养肺阴而润燥祛痰,并蕴陈氏补心生胃之意。合桂枝茯苓丸以化瘀血、行大便。加用青蒿鳖甲汤以透阴分之邪外出。用太子参、神曲以和胃安中,稍加浙贝母以增强化痰之效。 二诊时已无发热,唯有痰热未清,故加海浮石、胆南星等化痰清热。初诊因病人大便偏干而用桃仁,虽配合太子参、茯苓等安中健脾,但毕竟高年体弱,故二诊见大便不成形,故易桃仁为红花,并加山药以增强健脾助运之力。 02余某,女,25岁。持重劳累后,夜间骤起发热,最高37.8℃,服用解热镇痛药,热退而头痛,自服川芎茶调散,头痛不减,热势渐增,复测37.6℃,渐至咽痛,咳嗽,咽干口渴,痰少而黏,脉浮细,舌淡嫩,苔薄腻,微有剥脱。 析:骤起发热,不恶寒,咽痛咽干,属风热外感,当疏风解表清热,化痰利咽止咳。疏验方银翘升降散。 蝉蜕12g僵蚕20g连翘12g薄荷9g钩藤12g荆芥9g桔梗12g苏叶18g枳壳12g黄芩9g牛蒡子9g生甘草12g木蝴蝶5g淡豆豉30gX3付 一服尽,自觉热从鼻孔从,续服余药,咳嗽大减,复测体温正常,后体温未再升高,三付尽则咽干咳痰缓解,自觉好转未再服药。 按:风热外袭,本有银翘散正治,但原方解表、清解、顺气之力不足,现在也不能做到“时时轻扬”,因此对于明显的发热、咽痛、咳嗽等症状,尚显轻巧。故加蝉蜕配僵蚕,解表退热,薄荷配钩藤,疏风止咳,君药取淡豆豉及僵蚕,一可清透,一可解毒。 03评:发热为内科常见症状,按标准治疗当先分外感内伤,外感有风温、暑温、湿温、伏暑 秋燥、冬温、温疟,内伤有气血阴阳亏虚及痰湿、郁结、血瘀。若再往前推进,又有疾病的不同分别,普通感冒的发热,同大叶型肺炎的发热肯定不同,同麻疹、猩红热等传染性疾病的发热也不一样,至于血液疾病的发热、风湿性疾病的发热、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内分泌疾病的发热......很难一下说清。 如果按照《潜庵医话》那样,按照诊断学的目录,把发热完全按照感染、非感染等细分,添加进中药方剂和治法,恐怕仅有的药物又不能满足无限细分的西医病种。还是秦伯未先生说得好: “我曾经和学习中医的西医同志们讨论中医的退热法,他们认为,中、西医的退热方法各有所长,但中医的方法比较多,使用同样的方法时,中医方剂的作用也比较全面。例如发汗退热法,在西医临床应用范围较小,常用于一般的伤风感冒,对其他高热疾病偶尔用作减轻症状的办法,于病程无多大影响。而中医的应用范围甚广,不仅能改善症状,并且可以缩短疗程,不作为一般高热的姑息疗法。还认为,发热的后期患者多数体力衰弱,中、西医均采取支持疗法,但中医的支持疗法兼有治本作用,能使维持体力的同时,病理上也得到好转。” 所以在坚持辨病辨证基础上,秦老总结出退热十四法,颇有执简驭繁的作用。包括文中提到的三则医案,也在大的框架里面。 十四法包括:发汗退热法,调和营卫退热法、清气退热法、通便退热法、催吐退热法、和解退热法、表里双解退热法、清化退热法、清营解毒退热法、舒郁退热法、祛瘀退热法、消导退热法、截疟退热法、滋补退热法。 有些治法的概念是很狭窄的,比如调和营卫法特指桂枝类方,与辛温发汗不同,调和营卫是增强本身功能来祛邪外出,宜于体弱邪轻的患者。如果对一般伤风发热证,放弃发汗而强调调和营卫,也是不惬当的。 清气退热法特指白虎类方、黄连解毒汤,两者尚有甘寒和苦寒的差别,后者一般用于发热后期,出现心烦、错语等症。 有些治法的内涵是很丰富的,比如发汗退热法,实际已经包含了感冒的所有方剂。甚至根据温热性质的外邪变化,根据多种伴有发热的疾病的性质,囊括了半部温病学的内容。 如疟腮的耳前后漫肿疼痛,乳蛾的咽喉红肿,咽饮梗痛,赤眼的目红,迎风流泪,牙痈的牙断肿痛化脓等,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热。治疗时由于发病的部位和症状之特殊,在辛凉解表的基础上分别使用了柴胡葛根汤、甘橘射干汤、洗汗散和泻黄散等。 此三案中,主要用到的治法是发汗、清解、祛瘀、消导及滋补,一案抓久病腹胀、肌张力高、苔剥,主以消导、解表、养阴,二案抓午后及夜晚发热、咳痰舌暗,主以养阴、祛瘀、清解。三案抓咽干咽痛,主以发汗、清解,故难得取得如此捷效。 感谢耀夫供稿,欢迎讨论 奖小鲤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dougua.com/ddqyp/1689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隐秘的监狱荆州一狱警私带数万现金和
- 下一篇文章: 爷孙俩的中医故事淡豆豉篇之栀子豉汤